叶茵(1199~?)的名字,我知道得是比较早的。叶茵是同里历史上留名最早的诗人,又是同里所存桥梁中最为古老的思本桥的捐资及建造者。我作为一名同里土著,又是恢复高考后第二年录取的大学生,肯定对其有所耳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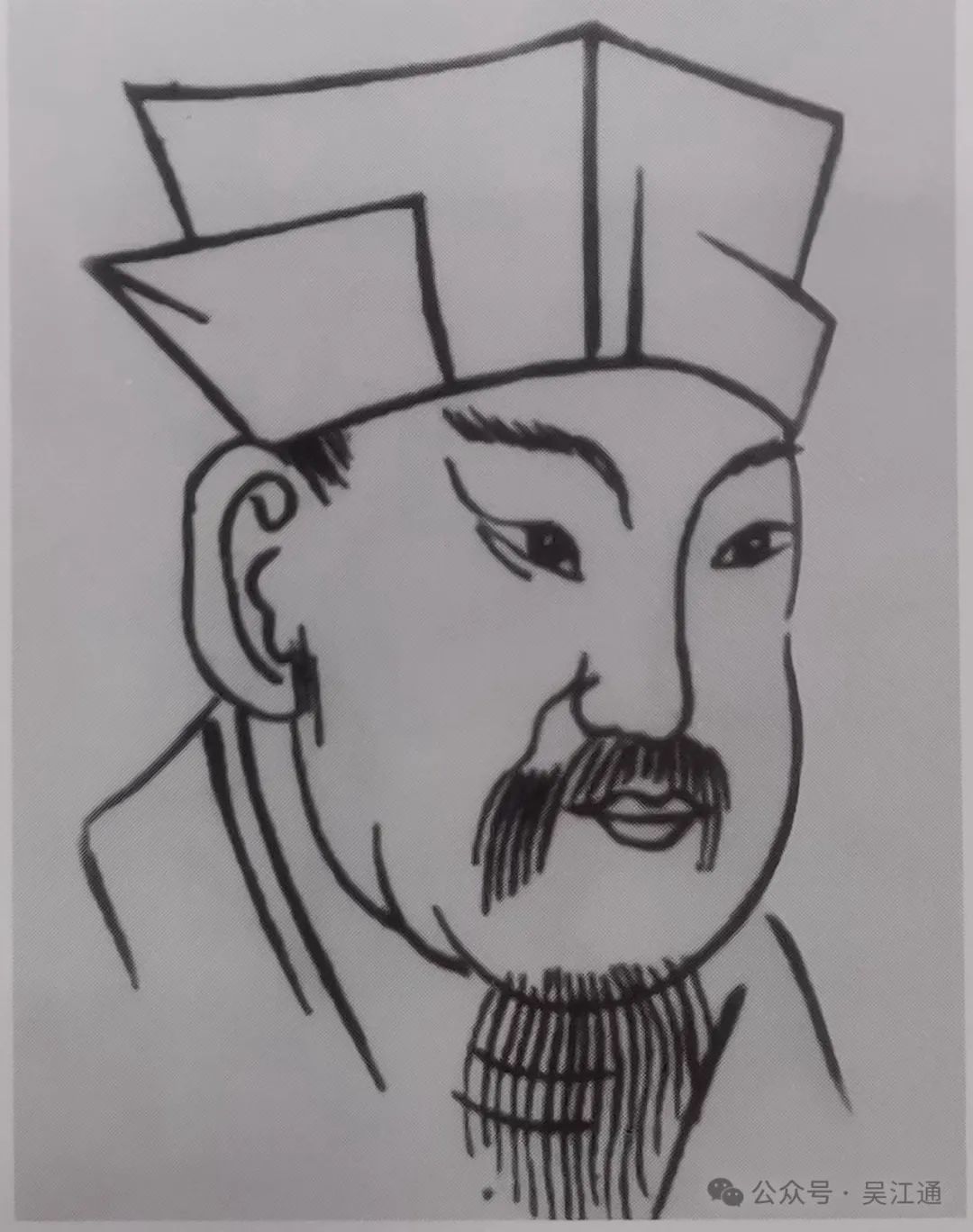
▲ 叶茵像 【摘自《同里镇志(增订本)》】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在红旗路上的书店里买了一本宋人七绝选本,发现里面有一首叶茵的诗《村居》:“数舍茅茨簇水涯,傍檐一树早梅花。年丰便觉村居好,竹里新添卖酒家”。读后静下来想想,位于同里南星湖畔的老家不就是这样的环境吗?
▲ 竹里新添卖酒家(左),南星湖一角(右)
两三年前,我开始步入耳顺之年,对国学及乡情民俗也产生了一些兴趣。某日上网查阅了叶茵的诗,并打印成册。粗略地通读一遍发现,叶茵的诗以田园、山水诗居多,除了上述的《村居》外,还有不少诗语言平实、清新,读起来却让人意犹未尽。如《山行》:
青山不识我姓字,我亦不识青山名。飞来白鸟似相识,对我对山三两声。
有人把这首《山行》与唐代诗人杜牧的《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相媲美,生活的恬静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跃然纸上。
叶茵出仕不顺,故返乡筑“水竹墅”,设“顺适堂”,常年隐居村里,他深知农民的疾苦。请看《田父吟五首其一》:
未晓催车水满沟,男儿鬼面妇蓬头。但求一熟偿逋(bū)债,留得粮粞便不忧。

▲ 水车车水(叶根弟提供)
诗中的“逋”字作“欠”解,粮粞即粗粮。诗的前两句表达了作者对农民劳作的怜悯与同情,后两句既反映了赋税的沉重,也透露出农民的无奈。
吴江自古便是桑蚕之乡,种桑养蚕也不易。《机女叹》一诗便是这方面的代表:
机声咿轧到天明,万缕千丝织得成。售与绮罗人不顾,看纱嫌重绢嫌轻。
诗人款款道来,不动声色,但心中的愤激、不平之情可见一斑。当初看到这首诗,我不由得想起初中学过的《蚕妇》:“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还有高中学过的《木兰诗》中的“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

▲ 黄道婆织布(叶根弟提供)
上述叶茵的诗都曾经进入某些中小学语文教辅用书或作为考题出现在试卷之中。
再来说说叶茵出资建造的思本桥。说来惭愧,工作以后虽然我也经常回老家,但由于种种原因实地探访思本桥已经很晚了。去年5月的一天,我退休在家已近一年,身为文史专家的原同事老孙约我去看思本桥,这才终于成行。

▲ 思本桥(叶根弟提供)
老孙开车来接我,在辽浜村里的一小块空地上把车停好,刚从当地某校退休的朋友老潘已经站在那里,一边抽着烟一边等着我俩了。我们一行三人沿着乡间小路向思本桥走去,前面带路的老潘忽然回头笑着问我:“老叶,问你一个问题,叶茵是不是你的先祖呀?”我说:“你这个问题我还真的思考过,从概率上来讲是多少有点可能的,但我三代以上都是贫农出身,几百年前的事今天还从何考证呢?”
说话之间,一座似曾相识的石桥便呈现在我们眼前,不用问,这就是思本桥。尽管我不是辽浜村人,不了解该村历史上的交通状况,但我猜想桥下的这条河当年一定是通向同里镇、流向吴淞江的。若要说思本桥的作用,借用叶茵写垂虹桥的诗句倒也没有什么不妥:“何年现采虹,悬足控西东。两地烟波隔,一天风月同。”思本桥贯通了该村与镇上的陆路,极大地方便了附近村民上街与做客。
在桥的东堍,立有一石碑,正面刻有桥名,反面有文字告诉我,思本桥建于南宋宝祐年间(1253—1258),全长22.5米、宽1.9米、跨度9米、矢高4.5米。全桥除桥栏板已遗失,石阶有小部分更换外,其余均为宋代原构。

▲ 思本桥石碑(叶根弟提供)
走到桥中央,感觉有点“吓咝咝”的,一是桥的高度不算低,二是两侧没有一根栏杆。造桥用的全是武康石,错落铺放在桥面上的两块超长石头最引人注目。石头的色差比较大,有的紫黑,有的浅黄;石头表面坑坑洼洼,有的还缺了半块一截,给思本桥增添了厚重的年代感。

▲ 思本桥桥面(叶根弟提供)
走到桥的西堍河边,朝思本桥的侧面看过去,有几块桥石上还雕刻出漂亮的乳钉纹,尽管尺寸不大,但十分亮眼。横向观之,思本桥给人一种对称之美、舒坦之感;纵向观之,拱形桥身与水下桥影构成一个大大的圆。我在想,若是月夜时分至此地,谁人不生“人境两忘天地寂,一声柳外咽新蝉”(《野堂即事》)之幽思?稍有不解的是,作为诗人的叶茵当年建桥时,为什么没有在两侧刻上桥联?像普安桥上那一幅“一泓月色含规影,两岸书声接榜歌”多好啊!

▲ 思本桥侧面(叶根弟提供)
从桥的西堍再返回到桥上的时候,我小站了一会儿。桥下小河,静若止水,已完全看不清它的流向,河的两岸则是野草丛生。朝西南方向看过去,是一大片闲置的田地,上有一个个瓜棚,下有一垄垄蔬菜,枝繁叶茂的树木密密地排列在小道旁边。再远处可见几幢半新不旧的商品房高高耸立着——正在我凝神远望的时候,听到老孙和我说话:“我刚才给你拍了几张照片,看你若有所思的样子,是不是想来这里造个别墅度度假?”只见老孙左手端着手机正从桥下大步走上来。我不假思索地答:“我不是与你一样?都是连老家都回不去的人,哪里还会有这样的念头呢?”不过嘴上这么说着,心里却在默诵“年丰便觉村居好,竹里新添卖酒家”这两句诗。

▲ 作者在思本桥上(叶根弟提供)
我上学读书的时候,生活艰苦。丰年给我的印象淡薄,村居于我的感受不堪。但近些年来,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我到过同里的北联村、汾湖的东联村、平望的村上长漾里、震泽的齐心村,还有庙港的开弦弓村。汽车在村道上行驶,整齐的树木、碧绿的田野伴着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村里的小河,尽是石头驳岸,清澈的河水泛着鳞鳞波光静静地穿村而过。人在村庄里走,只见农民自己建造的楼房宽敞又高大,前院可停车,后院可种菜。自来水、宽带通到每家每户。我对村居的感觉渐渐地发生了变化。
▲ 农村新貌
“松江之左,可渔可农。丁树阴阴,碧波溶溶。子契予好,携家而从。载笑载语,乃棹轻篷”;“我有旨酒,与子酌之。既醉且舞,且歌而诗。”叶茵在《别可山》一诗中描绘的村居画卷,在近800年后的吴江农村不仅随处可见,而且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更高的品质!
从思本桥上下来,在回去的路上老孙考我:“你知不知道思本桥桥名的由来?”我说:“这个难不住我。叶茵写诗,常怀乡恋之情、悯农之心;叶茵造桥,则取‘当思以民为本’之意。”老孙夸我回答得好,并继续说道:“看来,你的老祖宗叶茵还是有点情怀的。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中饭时间到了,我请你俩到百年老店公号酱园去吃面吧!”老潘反应非常快,说:“好!这个店新开张不久,面条不错,我来请客。”话音刚落,停车的地方已到,老潘先行发动汽车做引导,我还是坐在老孙车上,两车一前一后往公号酱园店徐徐驶去……

▲ 公号酱园·面馆